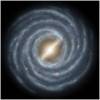Shi性大发:厕所与诗歌的美妙联系
利维坦按:和现如今厕所内找性伴侣和壮阳广告贴不同,过去人们在如厕时候留下的“真迹”除了屎尿,还有别开生面的文字,或者严格来说,是诗歌。诚如文中所言,在厕所,“一种临时的方式证明了数个世纪以来人类关心的特定问题的持续性”——不论是对于性爱的表达、男女关系上的偏见(主要是针对女性的物化),还是冷嘲热讽的政治观点,在这个臭气熏天的世界里,无疑都是最为真实的。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对于“正统”的反动:不论贵族还是平民,终究都在一坨屎上没有什么差别。这也算是原始的民间艺术对于“权威”的渗透和修订。
文/Maximillian Novak
译/Carlyle
校对/火龙果
原文/publicdomainreview.org/2019/04/17/tales-from-the-boghouse/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Carlyle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18世纪30年代早期,一位神秘的编辑(仅知其名为“Hurlothrumbo”)致力于印制一部不同凡响的选集:从英格兰的公共厕所中转摹涂鸦。这本鲜为人知的书叫《厕所涂鸦》(latrinalia),以通盘厌恶女性、恶臭肮脏的倾向,为乔治王朝时代的人们打开了一扇独特而迷人的窗口。
图自《快乐思想:抑或,玻璃窗与茅房杂谈》(The Merry-Thought: or, the Glass-Window and Bog-House Miscellany,1732年)第二版卷首页。
文学学者罗杰·朗斯代尔(Roger Lonsdale)曾表示,我们对于18世纪诗歌的了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诗选选择印刷什么。现代的一些选集反而集成了18世纪末期和下一世纪初期的作品,那时,其基本的理想内涵是“上流品位”。在一般的文化共识下,低俗、女性与政治时常被忽略。
朗斯代尔并不是唯一一位质疑正典基础的学者;事实上,在学术圈,修正主义很快就成为了一种精巧而实用的消遣游戏。现代读者不像18世纪末的编辑那样,对淫秽内容过分拘谨,或因单纯抒发个人情感的词句感到不适,并且我们很难单从这一层面上拒绝接受女性写作的诗歌。总之,我们赖以了解诗歌的选集已经过时了。
在那些不可能成为正统诗歌文学素材的作品中,J·罗伯特(J. Robert)集合了一些自1731年以来的内容,并将其分为四个部分出版,朗斯代尔曾经提过的这部《快乐思想:抑或,玻璃窗与茅房杂谈》,其简称《茅房杂谈》更加广为人知。
这部书在当时可以用“声名狼藉”来形容。詹姆斯·布莱姆斯顿(James Bramston)在他的《品位之选》(The Man of Taste,1733)一书中提到,这是诗歌中“良好品位”的极端反面例子。当然,只有在“上流品位”能够通过被自身排除的东西来定义自身时,它才具有意义;况且,没有什么东西比写在窗户上、刻在桌子上和题在英国厕所墙上的东西的集合品位更糟了。
正如现代作品《优质厕所指南》(The Good Loo Guide)的编者模仿一部著名的英国餐厅指南书籍那样,《快乐思想》不知名的编撰者也有一些模仿这个国家上流品位的念头——尽管这些念头是断断续续的。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和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难道没有因为他们的杂编而声名鹊起吗?又有什么是比代表着不同诗歌理想的诗集——一部被诗歌界明星宣称没有任何一首诗歌有艺术价值的、非诗人在空闲或绝望之际自然创作的诗集——更加令人惊讶的呢?
显然,一些创作者在如厕时会使用粪便作为其“题词”的媒介或主题【在某种程度上,这是T·S·艾略特(T. S. Eliot)声称所有诗歌都是一种“排便”形式的字面预兆】。《快乐思想》甚至不是德莱登(Dryden)在其《麦克·弗莱克诺》(MacFlecknoe)和蒲柏在《愚人记》(Dunciad)中批判那种艺术——坏诗人假装成天才完成的作品。
确切地说,作为一种或多或少自发的游戏或者激情行为,它是一种原始的民间艺术形式,只有在被一位受人尊敬的诗人创作,并且与这位诗人更为严肃的作品一同收录时,才会得到些许的尊重。正如现代的“系列”涂鸦那样,由于第一波“题字”往往能够激励后来人添上自己的一笔,它能够起到沟通的作用(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甚至可以将其看作是推特的早期化身)。
一个交流的例子。
事实上,涂鸦更加有趣的一个方面是,它以一种临时的方式证明了数个世纪以来人类关心的特定问题的持续性。对于涂鸦的研究往往集中于现代种族或国家之间的冲突、毒品问题和特定的政治时评。但是,除了这些地域性问题之外,现代涂鸦的内容与早期涂鸦惊人相似:对排泄物的观察、对爱人的惋惜、对女性性滥交的歧视性控诉、对“陈词滥调”的诗句和格言的重复,以及各种男人和女人暗示他们精通性爱和“可约”的信息。
并且,即使多年以来政治目标已经改变,许多政治方面的态度却仍保持不变。涂鸦是一种不够尊敬的形式,带有强烈的大众化与反建制元素。一切在所有阶层中都寻常的事情,比如吃喝、排便和通奸,都能在类似涂鸦的形式中找到它们的“低配版”记载。
从最基础的层面上说,一位涂鸦作者将会发现,富人的排泄物和穷人的排泄物没有任何差别。因此,有一首据推测是从“有生活品质的人的厕所”中收集的诗有着下面的感悟:
伟大的上帝啊!谁能想到,
这么优秀的伙计拉屎也会那么臭?
Good Lord! who could think,
That such fine Folks should stink?
这些观察结果从来没有什么“上流”的,也没有艺术的矫揉造作。严格说来,这些诗句属于民俗学与文学社会学,但是它们反映了对阶级层次的不满,和经历了罗拉德派和平等派后的某些底层阶层的平等主义态度。这些作品的作者是谁?他们真的是劳动者吗?或者他们只是来自于所谓“中产阶层”的下层?是否有证据可以表明上述群体的文字能力?
事实上,涂鸦也许会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识字程度的事情。有句俏皮话曾经指出,无论当时人们的读写能力如何,几乎每个人在面对茅房里的一堵墙时似乎都会文采飞扬:“因为每个来上厕所的人都写了东西。”对评论员而言,排便与写作之间的传统连结是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对照关系。有一首诗写道:
我们不承认自己做过什么恶心的事,
除了我们写的东西,和我们拉的x……
There’s Nothing foul that we commit,
But what we write, and what we sh – t.8
缺乏清洁后庭的厕纸或其他材料,也引发了下列一串连祷的感叹:
郁结于内的粪便,和顽固不化的智慧;
下流粗俗的韵脚,和脚下洞里的粪便;
那些抹着恶臭的粪便的墙壁啊,
都是那些不给厕纸的猪的杰作
拯救我吧——
From costive Stools, and hide-bound Wit,
From Bawdy Rhymes, and Hole besh – – t.
From Walls besmear’d with stinking Ordure,
By Swine who nee’r provide Bumfodder
Libera Nos—-
其他类型的涂鸦从非常炽烈的感情表露到,到与粪便无关的讽刺,题材一应俱全。其中更不走寻常路的诗歌甚至在歌颂忠诚而深爱的妻子:
我亲吻过她的端立,
亲吻过她的平躺,
亲吻过她的生机勃发,
亲吻过她的奄奄一息;
当她翩然而升起的时候,
我要亲吻她飞翔的模样。
I kiss’d her standing,
Kiss’d her lying,
Kiss’d her in Health,
And kiss’d her dying;
And when she mounts the Skies,
I’ll kiss her flying.
在这首诗歌下面,《快乐思想》对其情感进行了称赞。
一位女性抱怨自己在爱中的命运的诗则更显得情真意切了:
残酷的命运夺走了我的青春,
为他我在心里埋藏了一切的真挚,
我再也不会爱上谁,失望且不再寻觅——
人世间的坚贞不屈与坦诚相待。
1725年2月18日
Since cruel Fate has robb’d me of the Youth,
For whom my Heart had hoarded all its Truth,
I’ll ne’er love more, dispairing e’er to find,
Such Constancy and Truth amongst Mankind.
Feb. 18, 1725.
我们无从得知她为什么不能与她真爱的男子步入婚姻殿堂,但是她的痛苦似乎很短暂。这段文字下方紧接着一句冷嘲热讽的评论,说她是沃克家族的一员,作者坚称这个女人“像其他女人一样阴晴不定”,因为接下来的一个晚上“他”就吻了她。
这种对爱情和女性的玩世不恭,在《快乐思想》中占据着相当的篇幅。通常情况下,女性被描绘成“永远在性方面得不到满足的人”——比如在一个做完爱后休了一个月的假来恢复元气的男人如此写道。一个女人写了一首同样愤世嫉俗但表现更加现实的诗,抱怨丈夫经常使自己怀孕:
一个可怜的女子在一个危险的箱子中病恹恹,
她躺着,就像其他人那样:
上帝啊!她哭喊着,如果我的丈夫到来,
再一次带着他的情趣使我的下体欢愉,
我将电闪雷鸣,我将立下毒誓,我将如野兽般狂奔;
即使在下一个夜晚,他将同她和孩子一起度过。
S. M. 于1708年
A poor Woman was ill in a dangerous Case,
She lay in, and was just as some other Folks was:
By the Lord, cries She then, if my Husband e’er come,
Once again with his Will for to tickle my Bum,
I’ll storm, and I’ll swear, and I’ll run staring wild;
And yet the next Night, the Man got her with Child.
S. M. 1708.
S. M. 显然对于这个时代仅能使用最原始节育方式的已婚女性缺乏同情。女主角长期经受苦难的形象被男性随意的假设所削弱:生孩子并不是非常危险的事,女人放大了痛苦和困难。在那时,几乎没人想过要为女性生产创造一个无菌的环境,女人常常被迫经历十三四次分娩,这对于S. M.来说显然无关紧要,他认为女性对于再次性交的明显欲望足以成为蔑视她们的理由。
《快乐思想》中唯一收录的一幅图片,它显示了一个为爱上吊的男子。回应这幅图的评论中,关于图中的事是否能真的发生有一场相当规模的争论,“人比绞架还长”。(第二部分,第17-18页)
除了一窥社会态度,《快乐思想》还有很多反映此类作品功能的“题词”。在介绍1982年Augustan Reprint Society出版社出版的本书第一部分时,乔治·格非(George Guffey)教授提到了《摩尔·弗兰德斯》(Moll Flanders)描述的摩尔与她的爱慕者之间的求婚场景,后者后来是其第三任丈夫,也是她的亲弟弟。
在那时,像这样在酒馆窗户上的巧妙的求婚和回答是十分真实的。但是,《快乐思想》第二部分中的一次交锋却一点也不令人满意。女方对于她的倾慕者的说法感到愤怒,因为他在玻璃上写道,她意志的“标志”是“脆弱、狡猾而歹毒”,她反驳道:
我必须坦诚,仁慈的先生,尽管这片玻璃——
不能证明我的脆弱,但证明了你就是个混蛋。
I must confess, kind Sir, that though this Glass,
Can’t prove me brittle, it proves you an Ass.
尽管对于女性的物化和身体持续的动物本能,及简单粗暴的冷嘲热讽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如果有未来的人类学家只能依赖《快乐思想》作为这一时期的遗迹,它还是有足够丰富的内容能展示出18世纪的社会图景。
他们会看到一个更加忙于生物本能而非智力追求的社会——相比当时能够达到的儒雅、智慧的文学中描述的模样,这个社会更加在乎饮酒、爱情与排便。但是,他们也可以在剑桥书籍销售与出版商康尼(Corny)的讽刺尖锐作品中,找到书写求学与大学生活或批评歌剧的内容。他们会看到不计其数的年轻人渴望自己的情人对他们心软一些,以及对爱情失去幻想、愤世嫉俗的老男人。
但是他们也能从至今在汉普斯特德依然流行的烧瓶酒馆或卑微虔诚民间智慧中,得到一点直白的哲学。然而在更多情况下,他们将会发现,几乎没有一种普遍风格能够形容那时社会中即使最私人的正统诗歌。
许多作家确认了自己的身份以及他们爱恨着的女人的名字。简而言之,即使这些作品在其他方面成就甚微,它们至少真正展现了当时个人生活的生动缩影。在此程度上,将这些“题词”收入那时的选集里,提供了约翰·盖伊(John Gay)和乔纳森·斯威夫特等人创作的严肃艺术作品时活色生香的社会环境背景。
《快乐思想》第二版的题目页
这对开本对外宣称的出版者是一个叫“赫罗瑟鲁姆博”(Hurlothrumbo)的人,其名字来自于柴郡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一部戏剧作品。格非教授主张詹姆斯·罗伯茨(James Robert)“几乎肯定是个涂鸦收藏家”,这四个部分就是为他而印刷的,援引“赫罗瑟鲁姆博”是为了吸引一部分在塞缪尔·约翰逊和他的作品首次公开并演出两年后仍然受到的一些关注。
但是,我宁愿推测,罗伯茨本人不太可能是编辑中的一员,作品更有可能与塞缪尔·约翰逊有着更加直接确切的联系:可能约翰逊自己就是《快乐思想》四部分的汇编人。不管每个单独的拙劣诗人想表达什么,这个臭名昭著的涂鸦集锦——作为一部选集——同约翰逊其他作品具有非常相似的内核,那是难以想象的多样性、古怪的并置和本质上的无政府主义,其并非拙劣模仿上流文学,而是开辟了一种新的、几乎是启示般的崇高壮丽。
首先,《赫罗瑟鲁姆博: 抑或,超自然现象》(1729)这部书本身就是一部十分直接的滑稽模仿作品,作品形式混合着对话和歌唱,与盖伊的《乞丐歌剧》有相似之处,但却比《乞丐歌剧》更加狂野。约翰逊通过哗众取宠的戏剧成功抨击了当代悲剧的荒谬性,以及某些旨在展现恢弘画面的作品。
诸如“整个世界都是一场梦,一个域外空间,一个堆满钻石的茅坑”一类的台词似乎将隐喻的本质引入了拷问,尤其是当其与其他诸如“极乐世界是爱产下的卵,由一只放光的眼睛孵化”这样语无伦次的台词放在一起,或者和国王在思考同时饮下枪火和白兰地的效果时唱的下述歌谣并列时:
电闪从鼻孔里飞出
雷鸣自肛门中炸裂,而后唇齿崩坏,
有巨响声穿透天空,山摇地动。
Then Lightning from the Nostrils flies.
Swift Thunder-bolts from Anus, and the Mouth will break,
With Sounds to pierce the Skies, and make the Earth to quake.
《赫罗瑟鲁姆博》也许大多是无意义的,但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讲,它的无厘头是非常重要的。它显示了对一切戏剧惯例的反抗,并且与涂鸦拥有一些共性,其中就包括自发性。
如果约翰逊的目的仅仅只是相对不那么复杂的文学模仿,他本可以得到一些小的荣誉,这些荣誉足够让任何一批擅长讽刺既定文学形式的天才引以自夸,尤其是悲剧、史诗和田园诗。但是来自柴郡的约翰逊缺乏持续讽刺的审美距离,并且他的脑海中还有更加宏大的目的。
他沿袭的传统并非属于模仿家,而更像是幻想家——他是一个趋向于在同一部作品中融合高尚与低俗、恢弘与荒唐的神秘主义者。他并没有像菲尔丁(Fielding)在《悲剧的悲剧》(Tragedy of Tragedies,1731)中所做的那样,攻击英雄戏剧的夸张呐喊,或者像盖伊在《乞丐歌剧》(1728)中影射戏剧和田园诗;相反,他试着让自己的作品达到最高境界,尽管他并没有成功。他就像是蒲柏笔下的“飞鱼”,他“时而不时地扬起鱼鳍,飞出深渊;但他的翅膀很快又干了,只能跌回谷底”。
在其为《闪耀的彗星:抑或,诗歌的美丽》题作的序言中,约翰逊指出:“同样令愚者发笑的想法却会令智者叹息。”对于观众对其作品的回应方式,诗人给出了这样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他可以轻易跳脱出观众的嘲笑,向着他最为“恢弘”的诗句前行。
他经常做好准备“跳出忘我的境界,并将自己的笔触浸润在太阳里”。《赫罗瑟鲁姆博》中的一部分,尤其是火焰女神和野火(两者都被认为属于“发疯”的角色)之间的场景——野火威胁说他将脱掉自己的衣服并且“一丝不挂、赤身裸体地跑来跑去”——居然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Huckleberry Finn)中国王与长颈鹿的篇章有奇妙地相似之处。但是,不连贯的语言结构加上音乐与舞蹈,构成了一种既令观众发笑又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感到困惑的奇特混合产物。
约翰逊将“多样性”视为其最重要的艺术原则,他在《天堂的景象》(Vision of Heaven, 1738)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想法,这部作品与威廉姆·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天堂与地狱的联姻》(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图源:Nevsepic
约翰逊认为,所有的表面现象,都只是隐藏事物真实观感的“象形文字”。他的作品的讲述人有能力完成布莱克所谓的“精神飞行”。作品中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段落,星星被当作是向街上快要饿死的可怜孩子扔去的“冰冷匕首”;在另一个段落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挥舞着扫帚驱赶蜘蛛和所有威胁要靠近讲述人的年轻女子。神秘主义的气质通常能够在精神与排泄物、崇高恢弘与突如其来的“肛门中炸裂的雷鸣”之间建立联系。我们应该想的起来,布莱克也有描述自己排便的诗歌。
无论约翰逊究竟有没有编撰《快乐思想》,这些作品与他的名字有所关联的原因都一清二楚。尽管菲尔丁可能以一种明显降低自己的幽默和讽刺水平的方式,盗用了“Scriblerus Secundus”的名字,但是,《赫罗瑟鲁姆博》与约翰逊和他的作品之间的联系是如此之紧密,我甚至无法找出一个原因来证明,为什么他不可能是像《快乐思想》这样丰富、古怪的诗歌与散文集的编者。
然而,“多样性”与严肃的艺术没有什么相似之处,这应该和威廉姆·布莱克与约翰逊之间的区别一样明显。正如威廉姆·霍加斯(William Hogarth)所说的那样:“松散而未经设计的多样性,就是混乱与畸形。”
当然,杂集可能是以多样性原则组合起来的,这是它原本的特点。而真正使《快乐思想》有别于那些要求“上流品位”的作品的是情感的激烈起伏,正是这样的情绪波动引导着这些诗歌的作者,也抓住了编者的想象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些诗歌本身从对于粪便最粗俗的评论到对于爱情最炽烈的表达都各不相同。这首可能出现在厕所的墙壁上,而另一首可能被用钻石刻在玻璃上,这就是约翰逊所称的这一作品“象形文字”的意义一部分。
图源:Libre Théâtre
在约翰逊的戏剧里,总有着粗鄙与崇高、喜剧与严肃、讽刺与无稽之谈的奇怪混合体。如果他的戏剧与阿尔弗雷德·雅里(Alfred Jarry)的《愚比王》(Ubu Roi)有相似之处,那么一方面在于《快乐思想》就像雅里的选集,表明了人类灵魂荒谬的混乱;另一方面,约翰逊乐观地将这种混乱无序的人类思想与感受,看作是人类灵魂的象征。
往期文章:
“利维坦”(微信号liweitan2014)
微博:利维坦行星
神经基础研究、脑科学、哲学……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反清新,反心灵鸡汤,反一般二逼文艺,反基础,反本质。
投稿邮箱:wumiaotrends@163.com
合作联系:微信号 liweitan2018
点击小程序,或阅读原文进店
☟
1、头条易读遵循行业规范,任何转载的稿件都会明确标注作者和来源;
2、本文内容来自“利维坦”微信公众号,文章版权归利维坦公众号所有。